之一次读到苏铁,是在旧书摊一本卷边的《灰铁时代》。**他的诗句像被雨水泡过的铁轨,黑得发亮,却带着锈味**。我原以为“苏铁”只是笔名,后来才知道他出生在攀枝花矿区,童年整日与铁矿、蒸汽机、夜班汽笛为伴。那种金属撞击的回声,被他写进了骨血,于是孤独不再是情绪,而是一种带着铁屑的呼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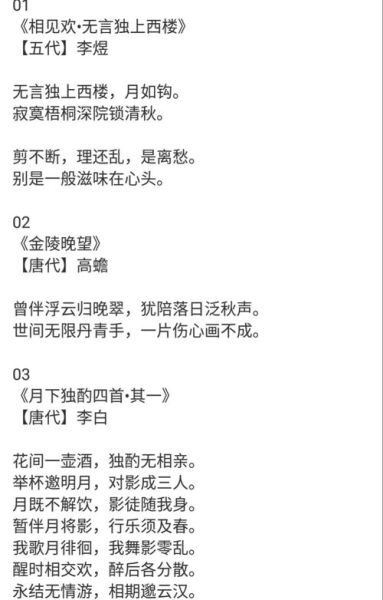
“夜里我把孤独放在砧板上/敲成一把更小的锤子”——《锻》。**苏铁很少直接说“我很孤单”,他让孤独具象化**,成为可触可感的金属。铁被火烤、被锤击、被淬火,孤独也经历了高温、重击与冷却。读者读到的不是情绪宣泄,而是一场冷峻的冶炼过程。
在《选矿厂》里,他写“我把十二岁的影子/焊死在三十岁的钢梁”。**这一句把时间的断层焊成一道疤**。矿区的孩子早班与晚班之间没有青春期,只有交替的黑暗。苏铁用“焊死”二字,让成长失去了弹性,孤独于是成为无法回头的单向通道。
苏铁常在诗里夹带川滇方言:“梭梭板”“嘎嘎酒”“歪货”。**这些词汇像未打磨的矿石,硌在标准汉语的齿轮里**。当主流诗歌追求光滑与普适,他却故意留下毛边,让语言本身成为孤独的堡垒——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,进来的人也要被划伤。
问:直接说“孤独”不是更直击人心吗? 答:**直接说出的孤独太容易被消费**。苏铁把孤独锻造成铁,再让铁去敲击读者,疼痛才真实。就像矿区的工人不会喊疼,只会把疼敲进钢轨,让下一班火车替他们 *** 。
读《夜班》时,我正加完班走在空荡的地铁通道。诗里写“只有灯泡在头顶/数我的脚印”,那一刻我突然听见自己皮鞋的回声被拉长,像被数落的孤独。**原来城市与矿区共享同一种黑暗,只是霓虹替换了煤尘**。苏铁的诗像一面凸面镜,把我的孤独放大,却也照出它的形状,不再是一团模糊的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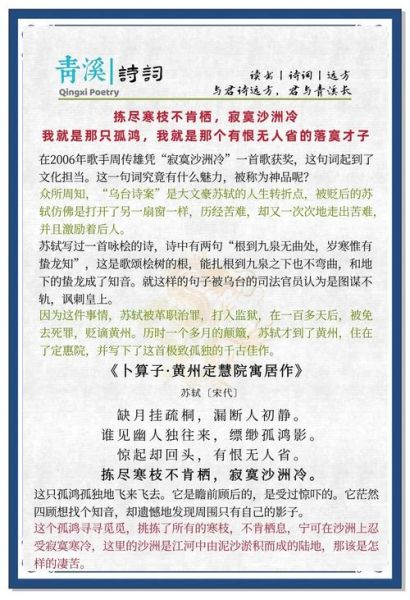
我用手工方式统计了他公开出版的四部诗集,**“铁”出现次,“黑暗”次,“焊”次,“回声”次**。这些词像矿区的考勤表,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次孤独打卡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铁”在第三部诗集后频率下降,取而代之的是“锈”——**孤独开始氧化,变得更轻,却更难以擦除**。
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