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之一次站在南京明孝陵石象路的秋色里,被两侧泼洒成金的菊花海包围时,心里冒出的不是“好美”,而是“它们在替谁说话”。后来我才明白,菊花从来不是单纯的观赏品,它更像一位沉默的翻译官,把中国人最说不出口的情感,用颜色、姿态与香气转译出来。

答案很简单:花期。当大多数植物在寒露之后纷纷退场,菊花偏偏逆势而上,在霜降前后盛放。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倔强,像极了我们对逝者的执念——明知人已不在,仍要在特定日子把记忆翻出来晾晒。于是:
我曾在祖父坟前摆过一盆墨菊,黑得发蓝的花瓣像极了他最后那件中山装的颜色。那一刻我突然懂了:菊花不是花,是记忆的容器。
陶渊明一句“采菊东篱下”,把菊花推上了“隐士”神坛。但有趣的是,后世文人跟风咏菊时,往往带着点自我催眠的意味:官场失意?那就“宁可枝头抱香死”;怀才不遇?便“一从陶令评章后,千古高风说到今”。
可当我走访开封菊展,看到卖花大爷用菊花拼出“中国梦”三个大字时,突然意识到:高洁早已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。对普通人而言,菊花可以是“我虽平凡但不随波逐流”的宣言,也可以是“日子再难也要活得漂亮”的倔强。这种全民共识,让菊花的高洁从文人自救变成了集体情感的出口。
多数人不知道,菊花在唐代以前其实是“爱情花”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,宫女“佩茱萸,食蓬饵,饮菊花酒”,为的是求子与求爱。直到宋 *** 学兴起,菊花才被“道德绑架”成君子符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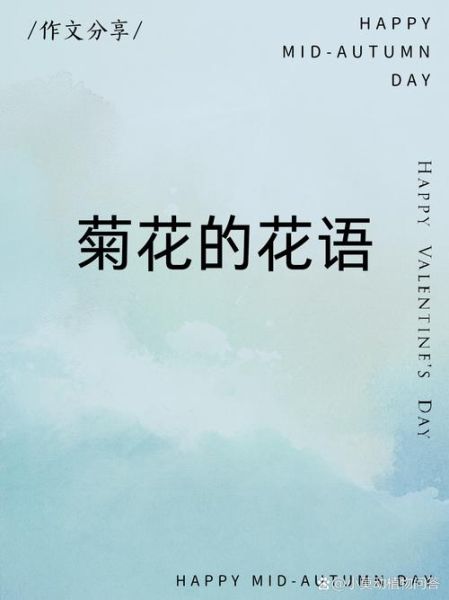
但民间的暗语从未消失:
去年收到过一盆红心菊,花心一圈绯红像被胭脂晕染过。送花人没说出口的话,菊花替他说了:“我所有的锋芒,都甘愿为你化成绕指柔。”
在心理咨询室,我见过一个案例:女儿与父亲冷战十年,父亲临终前每天往窗台放一朵小雏菊(菊科)。女儿后来哭着说:“他记得我小时候说雏菊像小太阳。”那些没来得及吵完的架,被六十朵雏菊温柔地画上句号。
这让我相信,菊花在当代的情感价值,早已超越“高洁”或“哀思”。它可以是:
答案或许令人不适:我们在借菊花逃避表达的笨拙。中国人太擅长“一切尽在不言中”,于是把未说出口的思念、愧疚、爱慕,统统塞进菊花的花瓣里。但真正的疗愈,发生在放下花的那一刻——
当你能直视父亲的眼睛说“其实我怕你失望”,当你敢对爱人承认“我嫉妒你的前任”,当你可以对自己说“不必做完美小孩”……那时,菊花才会从情感的替身回归为单纯的花。
而在此之前,请允许它继续当我们的“翻译官”吧。毕竟,有些情感太重,需要一朵菊花的轻盈来托举。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