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当一项心理学实验启动前,研究者都必须把方案递交给伦理审查委员会(IRB)。有人质疑,这是否只是“盖章”流程?我的看法是,IRB的价值在于“提前踩刹车”,而非事后补救。它要求研究者回答三个尖锐问题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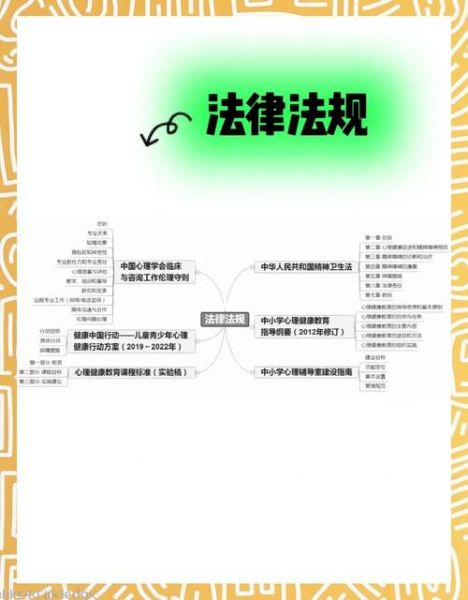
传统观念里,签字即代表“自愿”。然而,真正的自愿需要“随时可撤”与“充分理解”并存。我曾见过一项关于“社会排斥”的实验,参与者在填写问卷时突然收到“无人选择与你合作”的伪造反馈。尽管事前已签同意书,仍有被试在事后表示“如果早知道这么难受,我不会参加”。
自问自答:如何降低这种“事后后悔”?
答案:在实验前增加情绪预演环节,让被试通过简短视频或文字模拟最坏情境,再决定是否继续。
心理学史上不乏争议案例:斯坦福监狱实验、小艾伯特实验……它们共同暴露了权力不对等带来的伦理黑洞。对于儿童,需监护人双重同意;对于囚犯,需确认“不参加不会影响 parole”;对于抑郁者,必须配备现场心理师。
个人经验:我曾协助一项青少年 *** 成瘾研究,团队额外设置“情绪退出按钮”——被试可在任何时刻点击红键,屏幕立即跳转至心理咨询热线。结果,使用率仅,却显著提升了整体信任度。
删除姓名与手机号就足够了吗?2019年《自然》子刊指出,仅三条时空数据(如家庭、公司、健身房)即可重新识别95%个体。因此,现代匿名化需叠加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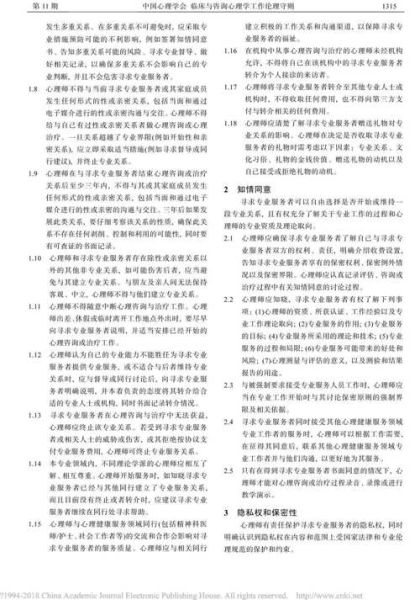
期刊偏爱“显著差异”,导致文件抽屉效应——大量阴性结果永不见天日。这不仅浪费参与者时间,更误导后续研究。我的建议是:在预注册平台(如OSF)公开假设与分析计划,无论结果如何都需发表。此外,作者需在文末披露所有资助方,哪怕只是一台免费提供的脑电设备。
集体主义文化下,“不伤害他人”可能优先于“个人自主”。例如,在部分亚洲地区,询问家庭冲突细节会被视为冒犯。此时,伦理审查需本地化:将“个人知情同意”扩展为“家庭协商同意”,并允许被试选择“跳过敏感题项而不影响报酬”。
当AI聊天机器人成为“虚拟被试”,是否还需伦理审查?目前,欧盟AI法案草案提出:若AI模拟人类情绪反应,仍需参照人类实验标准。因为训练数据源自真人,算法偏见可能放大伤害。下一步,或许会出现“算法IRB”,由伦理学家、数据科学家与公众代表共同审核。
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